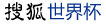新华社里约热内卢6月19日体育专电 题:球迷“婉约派”
新华社记者王子江
西班牙输球后,网上看去,或气愤填膺、或慷慨激昂、或痛心疾首,都令人感动。中国有这么多西班牙球迷,不清楚今天刚登基的西班牙新国王知道不?
在一片的愁愁惨惨凄凄切切的挽声中,一位同仁的随笔,将西班牙球迷的心声发挥得文艺非常:“繁华飘过,怀恋草长莺飞的时空,曾经坐醉的江山,而今岁月流转,愁绪难以描摹,于是你成了我滴滴答答的诗行……”
这些话婉约优美,可以用在譬如情书、家书、毕业、出国等各种场合,但的确寄托了作者对“斗牛士”告别巴西的伤怀。比起那些球队输了喝酒闹事巴不得将球员或教练拉下来自己上的“豪放派”球迷比起来,类似“婉约派”的中国球迷貌似更多些。“豪放派”球迷向前一步很可能变成有暴力倾向的足球流氓,婉约派向前一部可能变成诗人--当然诗人有时候本身就是流氓,只是玩得文武两样不同的把式。
任何球迷喜欢一支球队,都是因为个人生命中的某个节点,机缘巧合,碰撞上了心中最脆弱的神经。从此,球队成为记忆的一部分。以后与其说是观看该队的比赛,倒不如说回望生命中的自己,从中寻求自己内心的自信和平安。
英国历史上著名的火车大盗比格斯1963年因为盗窃260万英镑天文数字的现金,流亡巴西36年,2001年投案回国。他后来说到自首的原因时说:“我太想念回到海布里球场观看阿森纳比赛的感觉了,也时刻想回到伦敦的酒吧里喝上一杯苦啤酒。”
足球是心底深处最浓厚的乡愁,强大到足以融化比格斯这样的盗窃犯。有人觉得英国俱乐部之间历史性的对抗,是足球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但那是少数球迷耍流氓的借口。足球有它强烈对抗的一面,但它婉约的一面,更加吸引人。
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苏超冠军凯尔特人队与热刺队在伦敦举行了一场友谊赛,赛后我在地铁里碰到一位客队球迷。这位苏格兰人微醉,聊到英格兰队时,突然解下脖子上凯尔特人队白鸀相间的围巾,上面的几行字,中文大意是:“英格兰,老天诅咒你!你这个内心残忍的恶魔,你的所作所为让地狱里的魔鬼都自愧不如。”
苏格兰队与英格兰队是世仇,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内心的仇恨,将拔刀相向的愤怒化为文字,称得上是豪放中的婉约。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条因为出汗已经变得发硬和散发异味的围巾。
接触类似的足球文化多了,我自然也就变成了英粉。也是在10多年前,在比格斯魂牵梦绕的海布里球场,我认识一名叫希尔的文物商,他使用同一个座位看球长达30年。当年在海布里周围埋葬着很多老球迷的骨灰,阿森纳筹措新场馆时,也希望把球迷的骨灰迁走,但由于太多比较麻烦,于是出了一个告示,希望在新的场馆建一座纪念碑,把那些不能把骨灰迁到新址的球迷的名字刻在碑上。现在酋长球场已经用了多年,不知道纪念碑是否建了,也不知道那位当年采访过的球迷是否在新球场有了新座位。
始终觉得球迷之所以成为球迷,应该如阿森纳一样是双向的。球迷也不期望球队向他们“三叩九拜”,但诸如西班牙和英格兰之类的球队至少应该知道,在中国有一群喜欢他们的球迷,他们应该感激,应该找机会有所回报。
当然支持中国队就少点期望吧,因为那是我们共同的乡愁,我们的根。(完)2014/06/20 07:20
此稿为新华社体育专线稿件,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