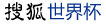苏亚雷斯咬人的瞬间,我抚着自己的肩膀狂笑:“咬了咬了他又咬了!”女儿在身旁先是捂上了嘴巴,过了一会儿幽幽地说:“苏亚雷斯小学时候牙非常难看,同学们都嘲笑他的龅牙,他就用它来咬他们,这样那些牙齿有了用处,就不会被嘲笑了。”
从荷兰咬到英格兰,从英格兰咬到巴西,女儿的话让我觉得苏亚雷斯不再有喜感,他成了一出悲剧的男主角,那出戏有关童年,有关成长。
由于想象力的贫瘠,我无从虚构苏亚雷斯的童年故事,但实在忍不住会想:他出生的地方普遍贫穷,土地坑坑洼洼。在一群孩子中间,他是个子最低的一个。他长得挺丑,拼命也合不拢嘴巴。他衣衫褴褛,永远抱着一个慢撒气的皮球。
每次分拨比赛,他都疯狂地进球,所有的孩子都拦不住他。最后大孩子气急败坏,把他按在地上,骑在他的胸口。他四肢完全无法动弹,唯一的战友是牙齿。他趁其不备,死命咬住一个孩子的胳膊,孩子的皮肤由白变青,由青变紫,由紫变红,被咬的孩子大哭,其他孩子松手,他闭着眼睛,死死咬住不放,直到大人赶来。
他踢得太好了,永远再跟比他大的人踢球,他盘带戏耍他们,他们推他搡他偷偷揍他,裁判从来不管这些,他的脑袋只能够着那些人的胳膊,顶多是肩膀。当他们用肘子捅他,他就侧过脸去,给他们的胳膊留下印记,签下自己的大名。
那时候没有摄像头,没有裁判,没有公正,他唯一信任的,不过是一双脚和几颗牙齿。
很多年过去了,那个一边进球一边撕咬的小孩,在飞奔中长高,成为疯魔苏亚雷斯。在他的眼里,看台上呐喊的几万球迷,不过是古罗马斗兽场的看客,脚下整齐的绿草,并不比坑洼的硬地亲切,对手不时瞟来轻蔑的一瞥,他决定给他们颜色看看。
女儿说她班上有一个男孩,是老师最头疼的学生。有天晚上野营,那个男孩突然尖叫着痛哭,说他妈妈是个女巫,但从来没告诉过爸爸,妈妈的同伙巫师现在要把他带走,窗外的灯光就是他们打的火把。
在我的记忆里,每个班都会有一个问题儿童,就像每个村子都生活着一个哑巴。在巴西,巴洛特利跳到对手头上,然后在场下哭着看意大利回家。佩佩用脑子轻轻蹭一下穆勒,趴在他耳朵说自己现在有点烦躁。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那些烦躁的小孩,正在寻觅一个个悄悄逼过来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