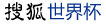|
| 孙贤禄在巴西世界杯球场 |
 |
| 中者为孙贤禄 |
 |
| 辽足时代 |
口述 孙贤禄 整理 廖旭钢
孙贤禄,第一个在巴西考取执业教练执照的中国人,他的儿子,是第一个在巴西青年联赛正式注册的中国年轻运动员。
在圣保罗采访孙贤禄,话题离不开中国足球史,更像是在梳理一本伤痛史,交谈中,无处不存在一种沧桑的感觉。
生于足球之城
我1964年出生,在辽宁大连,那是中国的足球之都。在我幼年记忆里,大连的民间足球氛围,并不比巴西的大多数城市差多少。
大连人为什么会如此喜欢足球?我觉得一方面,是当时的生活很乏味,没有电视机,只有个木头箱子的收音机,除了在空旷的大街上踢球,没有别的事儿可做;另一方面,大连,是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城市之一,因为她的殖民历史,让足球文化跟着许多西方人一起进来,大连人比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更早体会到足球的魅力。
哦对了,那个时候,大连不叫大连,还叫旅大呢。
学校只上半天课,下午呢,家住得比较近的孩子,组成学习小组,轮流在各家学习。没老师督着,我们一般看个一个多小时书,就“放羊”了,女生去跳皮筋,男的,就去踢球,去空地、草坪、海边、大街上踢。两块砖头往两边放好,就是个门,几个大孩子带着一帮小孩子,撒丫子玩儿去就是了。
大人也不反对孩子踢球,甚至有些鼓励。为什么呢?球踢得好,军区会招,大的国营厂会招,省队市队也会招,是条不错的路子呢。被招走了,就不用“上山下乡”了。
那个时候,大连踢球踢出名堂的人,是非常多的,就我们家那片儿,臧蔡灵(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脚)是我家邻居,他外甥女是我同班;徐建平(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门)家离我很近。那时,全中国还没兴起热爱足球的热潮,但在大连,他们已经是少年的偶像,是英雄了。
进小学之前,要上一年的“抗大小学”,相当于现在的学前班,上午学着写“毛主席万岁”,下午孩子们聚在一起踢球。而正经小学的体育老师,则会在球场教我们怎么踢,顺带挑一些好苗子,着重培养一下。
第一次听说巴西
联合路小学的陈峻老师,是我人生的一个老师。他脾气很好,有时候孩子在场上磕到碰到,他会直接抱在怀里,哄着骗着,把孩子哄笑。我们都很喜欢他。这是个让人尊敬的老师,他一辈子最大的梦想,是能培养出几个国家队队员——后来,我成了他成绩单上的一员。
每天凌晨四点,他就让我们起床,在公园里锻炼身体,练足球。
凌晨四点啊,东北的冬天,黑漆漆一片,路灯也没有几盏,我只穿一条秋裤,抖索索地下楼,老以为身后有什么东西追着我,撒丫子冲刺到公园,直到大家都集中了,才不害怕。好多孩子估计都和我一样,见面时上气不接下气的。
晚上回到家,还抱着球踢。我当时用头颠球,可以一口气顶四千个,脚下差一点,颠三千多个,这都是每天晚上,在路灯下面练出来的。我颠球不是最强的,同校有个孩子,跟人打赌,头颠球能不间断地颠一万个。那时的孩子聚在一起,比的不是谁家玩具贵,谁的家境好,比的是谁的球技更好。
在我小学所在的沙河口区,足球最强的学校,其实是临近的东北路小学,但是在我们那几届,联合路小学是唯一可以和他们抗衡的学校,这要得益于陈峻老师那几年的教诲和辛苦。现在,我估计国内是找不出这样的体育老师了,大家都不像过去的人那么“傻”了。
陈峻老师告诉我,有一个球星,叫贝利,踢球老厉害了,连脚后跟都能进球,他是个黑人,在一个叫巴西的国度。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巴西。
辽足王朝的骄傲少年
我们和东北路小学,是那一片区最强的两支队伍,也是老冤家,老对手,每次比赛,两队即使没有碰面,也憋着劲儿比净胜球。
后来,我被选去沙河口体校,然后进了市体校,逐渐走上专业运动员的路子,转头一看,嘿,队友都是老熟人,一半联合路小学的,一半东北路小学的。
我的队友,有不少现在还活跃在国内的足球圈子里,有孙伟(前绿城队主教练),有赵发庆(前重庆队主教练)等等。我们的老师是孙孝诚,他的脾气就比较暴了,不像陈老师那么温和,碰上有队员不好好训练,他是真的会动手的。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大家生活条件还比较苦,但为了能踢更多比赛,我们就到近一点的城市和省份,跟同龄人较量了。一般是我们训练有一点补助,再加上家长们掏点钱,凑路费,送我们到烟台、青岛等城市,和那里的学生踢比赛。我们背着铺盖卷,因为是暑期,也不用带太多衣物,晚上就睡对方的教室,把课桌拼起来就成。对方来我们这儿,也一样的。
1976年,我们本来打算去天津踢比赛的,后来因为大地震,去不成了,改成了去青岛。
1978年,我被选上了辽足少年队,李应发教练开始指导我。这里有个故事——其实,我原先不想去辽足,自己偷偷跑去沈阳军区试训过的,我还是想到军队里去踢球,穿着军装,多威风啊!对方也是想要我的,但是按照先后次序,必须是省队挑完了,不想要的人,才能进军区球队。
省队就省队吧,我刚到那儿,辽足就拿到了全国甲级联赛的冠军,当时开大会庆祝,沈阳的球迷都开心坏了,我也觉得没来错。作为小队员,我参加了庆功大会,记得很清楚,当时冠军的奖金,是每人120元人民币。
那个时候,辽足的人才非常非常多,像傅博、高惠臣、王洪礼等等,都是我们这一拨的。之后,辽足开始了全国称霸的历程,国家队里的“三王一郭”都是辽足的,我们辽足跟国家队踢球,可以不输给他们,甚至赢上一两个。
那段日子真好啊……每一个进辽足的人,包括我在内,都被教育说:你们是最强的,没人比得过你们。我从少年队到二线队,再到一线队,这么多年,踢了这么多场比赛,说实话,输球的还真没几场。在辽宁人看来,赢球不是新闻,输球才是新闻,我们当时的口号,是“只要第一,不要第二!”
噢,当时辽宁的足球记者,也当得很容易——比赛还没踢完,他们的稿子就在脑子里写好了,当然是赢,八九不离十。
足球进入金钱时代
从1984年开始,一直到1993年,我们辽足拿到了足协杯冠军,甲级联赛冠军,亚俱杯冠军,全运会冠军。“十连冠”啊,现在哪个球队,有我们那时候威风?中国第一届甲A联赛,我们辽足第一场球,进的第一个球,就是我踢的,对谁我忘了,我就记得那场球吹哨的是陆俊。后来想想,我好像进的是中国职业联赛的第一个球。
再到后来,辽足就不行了。1994年,我们没拿到冠军,联赛只得了个第四,1995年,辽足降级了。
你问我,辽足为什么会败得这么快,我也很难讲出个具体的原因。那个时候,全国的足球热潮都起来了,大家都疯了一样给足球送钱。大连队也开始起来了,你想啊,一个省份,企业就这么多,往足球输送的资金就这么多,大连队的钱多了,辽足的钱肯定就少了么。
再有,辽足的那一代人,有老了踢不动的,退役了,也有跑去大连的。1995年,辽足联赛最后一轮踢广东太阳神,我们赢了,但是另外一场八一输给四川,四川保级成功,我们降级了,而我,是全队年龄最大的一个。那一年,我虚岁33岁。
许多年以后,我在网上看到,有辽宁的球迷回忆,说我那场比赛之后,是全队哭得最伤心的一个。可能吧,我也忘了当时我哭成啥样儿了。我记得的是,那天晚上,我跟球迷、记者、队友一起去喝酒,喝了十几箱酒,我喝吐了,喝到神志不清,被抬回去的。
那些自费掏钱,跟着我们全国各地转的球迷,那些高速公路封道免费,欢迎我们归来的盛景,从那一刻开始,逐渐散去了。
在巴西的第一场比赛——0:11
1997年,我在辽足兼任队员和助教,联赛踢完,我就正式退役了。
全国对足球的热潮已经彻底掀起来了。我刚踢球那会儿,一个月有二十多块钱的补助,后来涨到四十多块,再后来一千多块,等我退役那会儿,我的月工资已经到一万两千块钱了。没过多久,我当起了教练,那时候队员,都按每场拿钱,一场十几万块,拿塑料袋装,一大包,扔过去能把人砸晕那种。
1998年,王宝山老师到云南红塔去当家,把我叫去帮忙。有一天他跟我说,俱乐部打算把青年队送到巴西去锻炼,可能要三年时间,想让你带队,你乐意去吗?
我当然乐意!一辈子的梦想,就是想去巴西这个足球国度看一看,多学点东西。
同年六月,我带着队员,踏上了去往巴西的飞机。我立下军令状,一定要把队伍带出个样子来。我们队要在圣保罗,和这里的青年队一起生活,训练,就住在圣保罗主体育场的旁边。红塔俱乐部,拿出三千万元人民币,作为我们队三年生活比赛的开销。
我和我的小队员们,接触到很多日后世界级的球星,像卡卡、拉伊、德尼尔森、卡福、巴普蒂斯塔……他们当时都在圣保罗俱乐部训练,在一个食堂里吃饭。而且跟我的队员年纪差不多,巴普蒂斯塔那时就已经很受关注了,卡卡很一般,当时还踢不上比赛。
中国年轻球员和巴西小球员的第一场比赛,是让我印象最深、也是最惨痛的——我们被打了个0:11,没有任何还手的余地。巴西球员最后都懒得踢了,自己下去休息,让队医上来跟我们玩,结果队医还真的进球了。
“中国人,玩‘乒奇乓奇’好了嘛,玩什么足球嘛。”一位坐在场边看球的巴西球迷,小声说的话被我听到了,当时我涨红了脸,真想上去把他揍一顿。
我们跟巴西的球队干过架
刚到巴西,接触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足球概念——巴西球员可以从后场起球直达前场,前场队员用冲刺的速度胸部停球,然后几下子就把我们的防线甩开,把球踢进门了,那种速度,那种精确,连我在内,都傻掉了。
在那之后,我带着队员,在三年时间里,踢了196场比赛,各种比赛都踢,从正规大俱乐部的青年队,到低级别的业余联赛。我们见识了像表演一样的足球,也见到了几乎每脚都会把人踢废的业余球风。我们跟巴西的球队干过架,几乎全队都上去了。后来,圣保罗方面派出的巴西教练,在打架后对小队员说:打架是错的,但既然开打了,就要全员都上,打输了更丢人!那些没打架缩在一边的,是没有团队精神,全队受罚,没动手的加倍!
我对巴西人的处理方法表示赞同。
在一百多场比赛之后,我们跟圣保罗青年队再次交手,他们就只能赢我们一个两个了,或许还会被我们进上一个。再没有看球的巴西球迷说怪话了,圣保罗这边,对我们取得的进步表示认可。
后来,我带着队伍回国,这支班底拿了两届全国俱乐部预备队联赛的冠军,在全运会上拿到第七名,这是云南三十几年里,获得的最好成绩,如果不是对八一的那场比赛,我们没踢进最后的那个点球,名次可能会更好一些的。
不过……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三年后回到云南,当时带队的教练是戚务生,那时的联赛,有整整两年没有升降级,我觉得这是对年轻球员极为难得的锻炼机会,向俱乐部提出,多让他们上场踢踢球,但是,没有效果。这帮球员,在冷板凳上坐了两年,差不多都废光了,唉……
其中有一个球员,圣保罗俱乐部甚至提出,要花钱买他,但是云南那边不同意,执意要带回去。但是回去了,也没球可踢,那个球员,现在都已经不踢球了吧。
我在巴西定居了
我拿到巴西绿卡,是很偶然的机会。1999年,我带红塔青年队去圣保罗的第二年,正赶上巴西十年一次的“大赦”,所有境内无身份的人员,都可以递交永久居留证的申请。我为了以后能来巴西更方便些,也为给自己多留条后路,就在当地华人的帮助下,填写了几张表格,交了上去,第二年,申请就批下来了,再过了几年,绿卡就正式到手了。
巴西的生活很舒适,让我最终决定,在巴西定居。这里的生活节奏比较慢,物产也极为丰富,早十年前,这里的菜市场到快关门时打折销售,一个十几斤重的大西瓜,1雷亚尔(相当于人民币3元)一个;四指宽、一米长的大带鱼,10雷亚尔二十公斤!一年四季气候恒定,每天都适合踢球。
噢,治安问题确实是有,我太太在里约的地铁站,被人抢过一回,脖子上的链子被拽走了;我和朋友有一次开车,碰上红绿灯停下,也被十四五岁的小年轻,拿枪指着要交钱。不过,这里的强盗有一点还是不错的,只求财,不伤命,你把值钱东西给他就行。
还是说回足球吧。2005年前后,我在成都五牛,在深圳健力宝队都当过助教。哦,李玮峰、李毅他们闹换帅,坚决要把教头迟尚斌换走那次风波,我就在队里当助教。后来,大家都知道,迟尚斌被排挤走了,我也就走了。
我一直很想,有一支真正让我执教的球队,哪怕差一点,二线队,都没有关系。不过,那时候的国内,让年轻教练出头的机会不多,我想了想,还是回巴西吧,继续学习也好,给自己镀金也好,总好过在国内,一直给人打下手。
2004年,我和帕尔梅拉斯俱乐部的前总裁儿子,合作在巴西搞了一个针对中国青少年的青训营,每人每年10万元人民币的训练费加生活费,一共办了四年,加起来一百多人参加,后来,青训营关了。
这个营,其实我是没赚到什么钱的,一个小年轻在巴西一整年,吃喝拉撒全算上,十万块换成雷亚尔,扣去成本,又能有多少剩下的。但是在国内,能出得起这个钱,让孩子来巴西学球的,又只能是家境比较好的那一批人。
我关掉青训营,最大的原因,是中国有钱人家的孩子,实在太难管了。不得不说,我在巴西这么多年,看过这么多业余的、职业的球员,没有一个是抽烟的。巴西球员极其自律,知道吸烟会极大地伤害自己的运动生涯。但是在青训营里,那些十几岁的孩子背着我偷偷抽烟,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动手打了人。
真正让我心灰意冷的,是几个孩子偷开了我的车出去鬼混,把车开进沟里,撞在树上。万幸的是,几个孩子都只受了点儿皮外伤。家长也都受了惊吓,把孩子叫回去了。从那以后,我知道了,这帮小祖宗,我真的伺候不起,他们那个样子,也踢不出来。
儿子说:爸,我不想踢球了,行不?
这些年,我在圣保罗开了家体育文化公司,顺带经营一些足球业务,比如把巴西足球队员介绍给国内俱乐部,或出席各种中国商业活动啥的。规模中等吧,你看这三层小楼,每层有近200平方米。约二十名员工,有巴西本地人,也有中国人。
有一件事情,是我到现在还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把自家孩子带到巴西来练球。
在我家孩子12岁那年,也就是2004年,我跟他说,愿不愿意去巴西练球,当时他很高兴地同意了。我带他到圣保罗、圣布尔纳多,还有巴拉那的青年队都去试训了,他踢中后卫的,虽然跟巴西的孩子比,技术比较粗糙,但好在他的站位、意识都不错。有巴西的教练跟我说,你家孩子是有希望的,好好练练,踢进中国国家队问题不大——那个时候,离中国队参加2002年韩日世界杯不久。
他跟内马尔同场竞技过,人家跟他同岁,那个时候就拿一万雷亚尔的月薪了,全巴西都看好内马尔。也不知是跟太多巴西同龄人比较,受了打击,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有一天,儿子跟我说:爸,我不想踢球了,行不?
我愣了很久,叹了口气:行吧,你要是真的不想踢下去了,就去读书吧。
其实,我是很想子承父业的。但是,很多事情勉强不来,而且中国国内现在的足球环境也越来越不好,或许……我孩子的选择,是正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