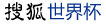我从不相信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伟大有过什么开端,那是天空和海洋的永恒,你可以试着把它读作18世纪初叶的莱比锡城堡,读作巴洛克时代最后的顶峰的辉煌,读作1830年门德尔松指尖的钢琴……也可以读作克洛泽略显老态的第十五次空翻。
生涯多舛的巴赫用严谨的数学公式,计算出一个民族纵横捭阖的澎湃激情,也用华丽庄严的设计,将自己的永生和所有人的一生勾勒于奥林匹斯山宫殿气宇轩昂的门廊。严肃的词汇,抒情的文学,《G弦上的咏叹调》亲切但难以解释,正如将雨的天空中振翅而过的普罗米修斯,纤毫毕现的英雄之美“只应天上有”。
德国足球是德国音乐富于困扰的延续,勒夫清朗英俊的指挥棒上,本应有着火焰藏而不露,有着胸怀博大轰鸣,还有歌德敏锐的耳朵在冥想,贝多芬聪慧的眼睛在倾听……但昨夜的不速之客并没有这相关的一切,面目全非的他肆意散布着无涯的嗟讶,留下了惊险的遗憾。
与自我肢解的葡萄牙截然不同,加纳人无边的天赋和阳光闪耀的革命精神,天真又危险。非洲足球的神秘无关神秘之处,只是忽略和遗忘——这是神秘最贫乏的形式,也是可怕。在巴伐利亚汗牛充栋的典籍里,翻来覆去也找不到任何与四年前狭路相逢相关的证据。于是,热罗姆·博阿滕发达的骨头染上了不幸的骄傲,被捆绑的双眼再也看不清同胞兄长凯文无动于衷的脚步和若有所思的力量;于是,赫迪拉和拉姆双双迷失在了无边暮色中;于是,瓜迪奥拉满怀好意地赠给勒夫那节奏轻快的jota,在没能催眠对手之前,先已迷失了交响曲固有的来历以及条顿战车关于胜负的方向。
克洛泽千呼万唤始出来,36岁的两分钟决定了一场比赛。当然,不止他一人,还有施魏因斯泰格,还有波多尔斯基,还有高举金杯的442阵型……这就是音乐,这就是诗歌,这就是德意志,请选择吧,他们全部都是!
在经过了这样一场交响命运的战斗之后,德国人迫切需要奏响下一个空翻的咏叹调。那不仅是回归,也不仅是超越,是属于日耳曼人的另一个光荣以及圣·托马斯教堂宁谧的午后,那奋力捕捉天籁精灵的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