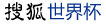往西飞的话,阿根廷、智利、乌拉圭还稍远那么一点点,但对中国人来说,这里已经是世界尽头了———巴西是这个地球上离中国最远的鼓励移民的国家。这里的中国人,每一个都有与众不同的故事。
“在这儿你必须要自己有过硬的实力,否则谁听你的?”
——— 圣保罗广州企业家协会会长宋远雄
宋远雄,51岁,圣保罗广州企业家协会会长,现在是他的第三个任期,他对这个事情非常热衷。
“十年前有一次被喊去参加一个广州商会的聚会,我一去就失望了,都是些什么人?踢着个拖鞋就来了,乌七八糟,我决心要做一个精英的协会。现在,我们这里都是各个行业能独当一面的人。”宋远雄对记者说。
“独当一面”成了入广州企业家协会的条件之一,广州籍贯则不必要。协会里有香港人,有上海人,有律师,有拳师,有商人。协会里最著名的是拳师李荣基,他在巴西开了70多家中国武馆,还被巴西军部聘为军校的擒拿教官。
巴西有形形色色的华人团体,宋远雄这个协会看上去比较成功,当然,这个利益平台门槛也不低。“在这儿你必须要自己有过硬的实力,否则谁听你的?谁跟你玩?中国人到了哪里都是中国人。”宋远雄说。
宋远雄是广州体院毕业的,毕业后在一所学校当老师,20年前在朋友怂恿下独自闯巴西,先打工,成家后自己开始做贸易,倒卖五金产品以及日常家用电器。这些产品来自中国,他在巴西贴了自己的牌子,批发卖,不做零售。“我现在很有成就感,一说这个牌子很多巴西人都知道,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中巴两国物价有天壤之别,倒爷找到路子后很容易发财。“从国内发一个货柜过来,现在全球经济环境不好,只要一千多美金的运费,但这些货(日用小电器),我可以挣十万到二十万美金。”他说得不夸张。一个淘宝上卖10块钱的那种最简陋的台灯,在巴西卖30巴币(约合90人民币)。巴西急缺民族工业。
宋远雄的仓库在圣保罗市区西南部,仓库超过一千平米,里面堆满了纸皮货箱。他们在楼上布置了一个广州企业家协会的专属办公室,墙上挂了一些协会成员跟广州市领导人的合影。不过其中有些官员已经在世界杯期间因为违纪问题被查而下台,宋远雄说他准备把部分照片撤下来。
宋远雄喜欢聊各色人等,从政客到商人,再到体育界人士。在聊到一个人的时候他比较来劲———巴拉圭乒乓球协会副主席罗满志。他所在的城市是跟巴西的伊瓜苏接壤的巴拉圭边境城市东方市,按照宋老板的说法,罗满志在那个地方相当有威望。“巴拉圭的警察见到他都要敬礼的。”
“罗满志在那边混得很开,因为他生意做得大,而且跟政府高层关系很不错。一般人是不能从伊瓜苏到东方市的,过不了关,但如果他开车带你过去,警察拦都不会拦。”宋老板用略带夸张但认真的语气说。
罗满志跟宋老板称兄道弟,在微信聊天中,宋老板拜托罗满志照顾好几个要从圣保罗去东方的朋友,罗满志用粤语回复说:“你交待的,我去做就是了。他们只要出机票就可以了。”这个回复让宋老板满面荣光。后来我们才知道,罗满志所在的那个巴拉圭边境城市,是很多巴西华人致富的地方。
“累是累,但一趟能挣500美金,你干不干?只要我多歇一天,就等于少赚一大笔钱。” ——— 皮包商人成老板
由于历史的原因,东方市有很多台湾人和香港人,两岸三地的华人聚集在那里可以发生足够多的故事。
南都之前报道过的52岁的广州人周开旗现在在圣保罗开照相器材店,他对东方市的回忆是这样的:前妻的舅舅在那边做生意,自己26岁那年抛弃了国内的工作跟怀孕的妻子去东方市生活。最初做修表工,被台湾老板欠薪,然后自己开修表店,再扩大为手表组装工厂。年入30万美金时,他回国探亲,而在香港做生意失败的大舅子回到东方骗去了他的所有财产。最后的结局是妻离子散,人生不得不从头再来……
在很多巴西华人眼里,伊瓜苏边境是一个冒险的地方,那里好像有一条进入巴西社会危险的捷径。来自福建福清的成老板是做皮包生意的,16年前他到了圣保罗,从巴拉圭的东方市批货,最开始是走私。“那边管得不严,军队和政府都很腐败。”
“刚来的时候年轻力壮,一周从圣保罗到伊瓜苏来回跑三趟,一个星期有6个晚上在火车上睡觉,只有1个晚上能睡在家里的床上。路上要跑15个小时。当时我们只需要两样东西:胆子、尿壶。路上很危险,晚上不敢停车撒尿,直接尿矿泉水瓶里。累是累,但一趟能挣500美金,你干不干?那时候巴西很缺货,只要我多歇一天,就等于少赚一大笔钱。”
现在巴西查走私越来越严,伊瓜苏和东方越来越以旅游景点闻名,而不是混乱无序的贸易通道。
成老板的货已经走正规海关了,不过他找到了避税的办法。“货到桑托斯的话,圣保罗州的关税很高。如果不着急,我一般让货走下面另一个州的港口,那边税率低,然后让一个皮包公司接下来,再让这皮包公司专卖到圣保罗给我。那样就可以避开圣保罗州的高税率。”中国人总是很有办法。
成老板20岁就有了儿子,现在儿子都14岁了。他说:“说实话,我在这边16年了,知道我家具体地址的朋友也就10个左右,我可以在外面喝酒,但真正很熟的朋友不多。有时候觉得老家好,但我们肯定是不回去了,我已经习惯了巴西。现在有亲戚陆续过来,像我老婆那边的一个弟弟,我要帮他在这边混好,他混不好,我回国探亲的时候哪有面子?不过只要他肯吃苦,不会挣不到钱。”
中国人的勤劳是显而易见的。在圣保罗最繁华的保利斯塔大道,世界杯期间巴西队比赛日全国放假,那些饭馆基本会关门,但中国餐馆绝不。
离记者所住酒店最近的一栋商厦里,有一家叫“华泰”的小快餐店,只有20平米,但这位来自北京的店主请了4个巴西员工。午饭10巴币任吃,周围10多家快餐店一顿至少在20巴币以上,所以它的价格是难以想象的便宜。老板明显是以量取胜,他总是忙前忙后亲力亲为,周六都会开门营业。
中国人在巴西的套路基本上是这样的:打一两年工,存了点钱,借点钱,开店,然后通过勤奋赚取第一桶金,越做越大……圣保罗著名的“25街”是中国商品的聚集地,这里的中国人像蜜蜂一样在商厦里修筑蜂巢,卖各种来自中国的小商品。密密麻麻的柜台铺面,当你置身其中,根本不会觉得是在巴西。这些货有些是走私的,有些过了海关。山寨机、仿真名牌表、包和鞋子的A货,应有尽有。看到中国记者,他们都不愿说实话,竟然吞吞吐吐说一双A货美津浓跑鞋的成本价是500人民币。能在这里租一个铺面开店,证明生意已经开始起步了。
有一天,广州企业家协会的副秘书长李兰带记者走这条街,路过街头一个推车小贩的时候指着她说:“十多年了,这个女的还在这儿卖这些小玩意儿,真的很罕见,中国人一般不会这么没有进取心的。”小贩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已经头发花白的瘦弱的中国女人,但看起来很精神,她的表情让人觉得她很满足于现状。但你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她宁愿在巴西摆摊而不是在中国摆摊呢?
巴西虽然没有城管,但警察收黑钱。圣保罗东方街“旺旺餐馆”老板告诉记者,他们每个月都要向警察交400巴币的保护费,如果不交就会有流氓来闹。
“我听他们说巴西不错,而且容易拿到身份,所以就过来了。” ——— 家庭旅馆老板于师傅
巴西很多华人的经历有特别之处。在宋老板公司附近,还有一个货仓,仓库里有个管理员是上了年纪的山东籍女人,她的丈夫曾经在台湾混过黑道,并被牵涉进了一起政治人物暗杀事件,所以逃到了巴西避难。
巴西离中国太远了,这里有较为宽容的入境条件,而且经济高速发展,被认为是一个开始新生活的好地方。
于师傅来自江苏徐州,曾是IT工程师,现在他的工作比较杂,是家庭旅馆老板,也是私家出租车司机,还利用自己巴西国籍的身份帮助中国人办理移民。他不是直接从中国到巴西的,更不是那些亡命之徒和偷渡客,他是因为在法国呆不下去了,一路往西走。
“我(上世纪)90年代初在深圳工作,一个月500多人民币,后来公派出来到法国留学,就留在法国了。但在法国搞不到身份,只能黑在那。当时能出去的人一般都不会回国,中国那时候太穷了,要拼命留在外面。我听他们说巴西不错,而且容易拿到身份,所以就过来了,因为留在法国没什么指望。”
当地政府每过十年左右就会归化一批黑户,华人把政府的这个举措称为“大赦”。入境后在这里待超过5年,政府在大赦的时候就会给外国人巴西国籍。于师傅刚好到了巴西的第5年遇到大赦,他前5年都没有离开过巴西,因为一旦离开,回来之后入境累计时间又要重新算起。
巴西鼓励移民,还有更简单的拿到国籍的办法,生小孩或者开公司。只要在巴西有了小孩,一年之后父母双方都能拿到巴西国籍。如果在巴西投资开公司,只要有了一年的缴税记录,也能入籍。于师傅现在的工作之一,是帮那些试图投资移民的中国人当企业法人。
“中国人要在这里开公司,首先要在当地找一个有巴西国籍的人做法人代表,法人身份至少要维持一年。我一年收5000美金,但这个钱也不好挣,三年前我给一家公司做法人代表,结果他几个月后就撤资走了,我是收了5000美金,但他们在巴西雇用的几个员工把公司告上法庭说欠薪。我是法人啊,所以都算到我头上。法院罚了我三万美金,亏大了。这钱我还没找那家中国公司要回来,我现在已经很小心了。”
于师傅20多年前从法国到了巴西,娶了一个巴西当地女人做老婆,生了一个混血儿子,后来离婚了,儿子跟他过。现在他有个女朋友,是一个曾在中央音乐学院读过书的单身妈妈,她在美国待不下去,也跑到巴西来了,他称她为“战友”。
于师傅跟这个女朋友合买了一套房子,改造成了家庭旅馆,一个床位平时卖20巴币一晚,世界杯期间涨价到40巴币。
(球票)本来我想高价卖掉的,但想想一辈子可能就这么一次机会,咬咬牙没卖。——— 葡语翻译任义
巴西在19世纪就有了第一批华人移民,最近30年移民陡增,第二代巴西华人已经形成一个群体。
记者在巴西接触到的第一个华人是我们在里约热内卢雇用的翻译任义。任义今年24岁,皮肤偏黑,戴一副眼镜,个子不到一米六,背稍微有些弯,肩膀总感觉要往下掉。他脸上有些青春痘,粗略看上去有一层油渍。
从神情上看,他像一个刚毕业的来自中国内地县城的家境一般的学生,他全身上下唯一有巴西特色的是他牙齿上那一圈绿色的牙箍。最近巴西人很流行用这个给牙齿做矫正。
任义是在巴西出生的,他的父亲曾在北京大学教书,母亲是医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夫妻俩移民到了巴西,投靠了任义当时已经在巴西定居的舅舅。他不太愿意聊家里现在的情况,但隐约透露过父母到了巴西后自己转做生意了,国内的社会积累不得不抛弃。
对于他自己的工作,他只是说:“在一家中国企业打工,平时比较自由,有时候要出差。我来做翻译是请了假的。”
那几天在里约,他的临时住所在马拉卡纳体育场附近,那片区域比较偏僻。有天上午他走向地铁站的时候,还被两个黑小伙儿抢了(南都曾有报道)。他把身上的钱乖乖给了他俩,但说服了对方不要拿走他那部用来跟朋友联络的手机。那是一部旧的华为手机。
他自己描述当时的情形:“他俩拦着我,我没搭理他俩走了过去,本以为没事了,结果他俩又追了上来,其中一个把衣服撩起来,腰里别着一把枪,也不知道真枪假枪。当时周围没什么人。”任义看起来确实好欺负,他标准的葡语,那天刚好穿的一件巴西队盗版球衣,都成不了救生符。听巴西华人说,东方面孔的人在街上被抢的几率比较高。
在圣保罗那场荷兰打阿根廷的半决赛后,记者又碰到了任义,他说他之前在网上订票,唯一订到的就是这场半决赛的票。“本来我想高价卖掉的(这场球一张票至少卖2000美金),但想想一辈子可能就这么一次机会,咬咬牙没卖。可惜阿根廷进了决赛,我们都不希望看到阿根廷人在我们国家踢决赛。”他有着绝对的巴西人的立场。
一路上他手里拿着几个套在一起的饮料杯,这种杯子是在场内买饮料时附送的,很实用,也有纪念意义,他从其他人手里要了几个带回家自己用。他说书包里还装了几个更好的杯子,上面印着比赛时间和对阵双方。
在中途某个站,任义在夜色中匆匆下车了,他要去换乘大巴,他家住在圣保罗往里约方向去的另一个城市。他身上全是中国痕迹,但有一点跟巴西的其他中国人很不一样———他好像不喜欢扎堆,总是独来独往,有那么一小股书生气。